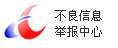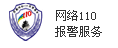下乡散记
40多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将我卷进了义乌尚阳公社莱山村,老老实实修了几年地球。青春年少的躁动和初涉世事的无奈,在我的心里镌刻着对那段岁月永远难忘的回忆。是苦?是乐?是酸?是甜?很难分辨清楚。不经意间自己像做梦般老了,当年接纳我“再教育”的山村,也再不是义南山区的穷乡僻壤了。
我的人生平平淡淡,梳理了一下,只有“上山下乡”这段经历还有点后味,我也一直当做宝贝来收藏。
房子
当初选择这个离古镇佛堂20多公里的山村落户,完全是因为这个村子虽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但是在我们安排落户的生产队中,它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听公社的同志介绍,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村前大片新开垦的茶园,是这个村子今后的一个大元宝。
对于一个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归宿的。那天在公社大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村里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把我领走了,我挑着铺盖跟在他身后。快进村时,在田畈劳动的社员们都停下活儿,好奇地看着我,让我很不自然。
村干部把我带到一间有楼的厢房,告诉我这是分配给我的房子。也就是说,从这天开始我就住在这儿了。我仔细打量着这间暂时属于我的房子:这是一间古旧的木屋,光线很暗,地面潮湿,四周都是被烟熏黑的板壁,一个旧三眼灶台,刚用石灰水漂白过。无疑,这房子不久前还有人住过,他是谁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怕我人生地不熟,村干部找来一个憨厚的后生与我做伴。
我很快打听到,几年前,村里发生了一起轰动当地的冤假错案,如今虽然风平浪静了,但由此产生的伤痛却永远留在村民们的心里。我所住房子的房主、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因为爱说公道话,被人诬告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受不了逼供的折磨,在夜色的遮掩下吊死在这间房子的横梁上,房子也理所当然地没收了。因为村里没有多余的房子,简单地被粉刷了一遍之后,就用作知识青年的栖身之处。
我这才明白,村干部为什么要给我找个小青年做伴,一直到几年后我离开这个山村。
工分
种田人看重的是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气换来的那几个工分,那是养家糊口的依靠,在那个“吃饭靠集体”的年月更是如此。
因为我比生产队的其他人多几滴墨水,初来乍到的也扯不上什么亲朋好友,同任何人都没有亲属关系,在一年一度的队委推选中,我竟以高票当选为记工员。社员们事后说,你做人稳重,做事公道,我们都相信你。
我会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的,再说在每个人的名下如实地记下他们的劳动内容和每天应得的工分,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可老百姓却不这么认为,每天吃过晚饭,男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手里捏着一杆旱烟斗,女人们则夹着一只布鞋底纳着,很有心计地看着我把一天的工分记好。隔一段时间就拿出上面记着一串串数字的皱巴巴的历书,与我核对,直到我的工分册准确无误以后,他们才放心地离开。
我完全掂量得出这“记工员”差事的分量,生产队长每天安排好活以后,我就应该留意这千变万化的分工,到晚上详细地记下来,一年到头都是如此。
当黑夜来到山村,孤寂中的我总想,看来我要在这穷山沟里接受一辈子再教育了,也很难推掉这记工员的差事了。既然成了一朵公社的向阳花,我也只能为了那几个工分,义无反顾地向农民学习种田了。他们一代代都能靠摆弄泥土度日,我这白面书生也应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缩短与贫下中农的距离”。我对农民并没有偏见,因为自己目前也是一个农民,只不过在公社集中学习的时候多了一个“知识青年”的头衔而已。
防空洞
那天,村干部从公社开会回来,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要打仗了,上头要求村村挖防空洞,规格要尽量高一点,到时候要藏人的,它可不是贮藏番薯的地窖。
这是头等政治大事,全村雷厉风行地动起来了。洞址就选在村后那块向阳的黄土坡上。谈不上工程的设计,也没有军事秘密,叫上几个三代赤贫的基干民兵,背上沉重的开山镐,听书记上下比画一番,就一镐下去,动起土来。
祖辈们都是在连年的战火中过来的,他们的生命经历了太多的劫难,也遭遇过失去亲人的痛楚,故此,对那些专门与中国人作对的外国人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大家每天都关注着民兵们的挖掘进度,也经常结伙光顾这个未作任何加固也没竣工验收的洞穴,听教书先生讲解原子弹掷过来时应该如何有效地在防空洞保护自己。
防空洞在山体中弯弯曲曲地前进了三四十米,洞口的新土堆满了好大一块平地。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村民们瞠目结舌的大事,有人出事了。
上头要来检查防空洞的进展情况,形象工程嘛,总要将洞口用砖头砌一下,可村里一时又拿不出过多的钱买砖头,民兵们只能到坟堆里拆坟头砖了。他们图省事,也不扒去上面的厚土就一头钻进墓穴拆砖了。这下可闯祸了,墓顶塌了方,压着了人。当费劲地将被压的人从土里扒出时,这人的脊梁骨断了,他非常困难地喘着气,经抢救虽然捞回一条命,可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时,村里流行着一种说法,说是挖防空洞触犯了山神,掘祖墓冒犯了祖宗,一切都是报应。
以后,仗没打起来,黄土高坡上的防空洞一直闲着,没藏过人。因洞太大,也没贮藏过番薯,倒是有人躲进洞内拉过一大堆屎。
标语
那时候种田人学习的榜样是“一大一小”,大的是大寨,小的是小靳庄。一个是开山种谷,一个是唱歌唱曲,各具特色。村干部找上门来,要我在村舍的几个主要地段写几条标语宣传宣传,造造声势。
我在村里的各条巷子里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一块适合写标语的平整墙壁,村里都是年久的土墙,长年的风吹雨淋在上面写满了山里人的艰辛。要在这些凹凸不平的墙上抹一层泥浆,再刷上一道石灰,成本太高了,大家没法接受,只有晒场边一长溜新建的仓库后壁才是写标语的最为理想的场所了。
那几天我不用下田,提着一副三角板在刷过石灰的墙壁上画格子,再在这些格子里描上并不规范的美术字。当那些大红油漆在山里人的墙壁上、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变成一条条火辣辣的标语时,我发现他们除了满脸的漠然,看不出有丝毫的激动。我明白,他们每天最关心的是手中的饭碗里究竟掺了多少番薯叶和萝卜丝;冬天到了,该往自己的硬板床上铺一层干燥的稻草了……
仔细辨认,村里以前一直有过各种不同内容的标语,除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外,还有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把农民组织起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办钢铁,赶超美英”、“讲卫生,除四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颜色较为鲜艳的是在对称的葵花图案上描着三个“忠”字,还有排列整齐的四个“伟大”等等。
标语是反映一个时期的行动口号,也是人们意识形态里的思想指南,在山村的风雨里它会褪色或者被新的标语所覆盖,但在我记忆里始终是清晰的,它的脚步总是那么沉重那么有力,奏响生命的交响曲,写在土墙上的标语和住在土屋里的人也始终在晨光和晚霞里融洽地相处着,还有他们憨厚的牛。
守山铺
生产队的林子是在离村很远的大山深处,所谓守山铺,要对付的是人而不是野兽。大炼钢铁时,毁了大半的山林,使村子周围的低山只剩下几根“瘌头毛”了,人们烧饭用的柴禾要到很远的山上去砍。裸露的山崖上用石灰水刷上了封山育林的标语,仍然挡不住山民们盗伐山林的脚步。为了使集体的林木不受损失,队里的所有劳动力都要轮流上山守山铺。
山铺搭在山梁上,砍几根现成的木料,再铺上一层松软的干草,就成了一座简易的房子和一张简易的床了。第一次守山铺,我是和朱伯一起上山的,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我们站在山梁上巡视,群山尽在我们的眼底。看见有人走进我们的林子,我们直起嗓子高喊几声,劝他们赶快离开。
比起山下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这守山铺就显得轻松安闲多了。我悠闲地哼起了小调:“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远离尘嚣,这山沟沟里吹来的风特别的清新凉快,也暂时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种戒备和火药味。山上没有高音喇叭,只有虫吟鸟鸣,没有火辣辣的标语,只有万紫千红。
到了该烧饭的时候,朱伯烧起一堆火,我用竹筒从山涧里背来泉水,在铜罐里烧了满满一罐饭,筷子是用现成的竹枝削的,菜是从山下带来的干菜。这是地地道道的野炊,别有一番风味,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那种恬淡、平和与超脱。
太阳沉到山后去了,夜,来到我们身边,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还有几分孤单。
半夜醒来,山风怒吼,林涛声声,冷月当空。
我有些恐惧,心想这时如果有一只野猪窜进来,我们能对付得了吗?我们手边只有一把柴刀啊。
朱伯说,安心睡吧,没事,人怕野兽,其实野兽更怕人。
- 没有相关新闻!
①义乌乡村在线上发布的所在信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义乌乡村在线”或“来源:http://www.ywxc.com”。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本网转载其他媒体稿件是为了传播更多的信息,此类稿件不代表本网观点。如果本网转载的稿件涉及您的版权、名誉权等问题,请尽快与本网联系,本网将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妥善处理。